
聶紺弩
從上海到延安,一次遂愿之行
在上海北四川路與竇樂路交叉口,有一家標志醒目的“公啡”咖啡店,坐落在老上海公共租界邊緣、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上。店主為挪威人,經營此店已有幾十年歷史。咖啡店為兩層樓結構。樓上為西餐廳,臨街是一排寬敞的落地玻璃窗,街市的熱鬧一覽無余。
1936年9月的一天,在“公啡”咖啡店二樓,有兩人相對而坐,私語竊竊。從他們并不輕松的神態中能感受到所涉內容的非同一般。其中一人是受中共中央派遣在上海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馮雪峰。另一位則是時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上海滬西區大組組長的聶紺弩。正是這次約見,馮雪峰交給聶紺弩一項特殊的任務:護送丁玲前往西安。
作為著名左翼作家的丁玲此前曾遭國民黨特務的綁架和軟禁,在馮雪峰等人的精心策劃下,丁玲終于沖破藩籬,獲得自由。根據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決定,丁玲將轉道西安秘密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考慮到此行的安全,故選擇了左聯同仁聶紺弩同行保護。聶紺弩慨然應允,告別了已懷身孕的妻子,秘密離滬。
這次任務很特別,聶紺弩與丁玲以夫妻作掩護,一路有驚無險,安然抵達。在西安,他們見到了前來聯絡的潘漢年。聶紺弩完成任務,心殊釋然。眼見丁玲將前往保安,聶紺弩突然意識到神往已久的中共中央所在地竟近在咫尺。他隨即向潘漢年表達了亦想前往保安的愿望。但潘漢年還是要求他返回上海。因為上海地下工作需要他,而他的妻子仍在上海,一旦身份公開恐受連累。
聶紺弩只好折返。途經南京時忽聞魯迅逝世噩耗,他立刻乘火車趕往上海。大師遠行,山河失色。聶紺弩隨即融入到萬國殯儀館的悲慟人群中,并與蕭軍、胡風、黃源、巴金等成為魯迅出殯的抬棺者。以后,他曾以題為《一個高大的背影倒了》的新詩來謳歌魯迅并寄托他的思念。
1937年8月13日,黃浦江畔的槍炮聲揭開了淞滬戰事的序幕。上海這座聞名于世的大都市經歷了一場血與火的洗禮。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堅定的抗戰信念、上海軍民的同仇敵愾、謝晉元部堅守四行倉庫以及女童子軍楊惠敏泅水獻旗等,濃縮了淞滬抗戰的激情畫面。作為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員的聶紺弩很快便融入抗日救亡洪流中。但最終上海還是淪陷了。面對殘酷現實,聶紺弩參加了上海救亡演劇一隊前往武漢繼續抗戰宣傳。同行中有馬彥祥、賀綠汀、宋之的、塞克等。
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是長江中游的一個重要城市。抵達武漢后的聶紺弩,強烈地感受到一種迥異于其他城市的地域激情和彌漫其間的抗戰氣息。演劇一隊在武漢三鎮進行街頭宣傳演出,以《放下你的鞭子》為代表作。一時觀眾如潮。聶紺弩沒有演劇才能,唯有繼續寫作。當時胡風主辦的《七月》雜志成為聶紺弩的重要陣地。不久,聶紺弩受命主編《新華日報》副刊《團結》。對于曾經主編過《動向》《海燕》雜志的他來說,這可謂專業對口,也駕輕就熟。但很快又有了變化。次年初,根據組織安排,聶紺弩與艾青、田間、蕭軍、蕭紅等前往山西臨汾民族革命大學任教。
令聶紺弩頗感意外的是,在臨汾他居然見到了丁玲以及他的老鄉也是他入黨介紹人吳奚如。原來,丁玲、吳奚如正率“西北戰地服務團”在臨汾演出。故人邂逅,不禁大喜過望。然而這種陶醉很快便被戰火硝煙所淹沒。其時,日軍攻下娘子關后,正由晉北南下。臨汾首當其沖。形勢危急,聶紺弩以及一幫“教授”們即隨丁玲、吳奚如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一道緊急撤往西安。
這時候的中共中央已經從保安遷往延安。來到西安的聶紺弩又一次感覺到與黨中央所在地近在咫尺,一種強烈的地域魅力在吸引著他。在十八集團軍駐西安辦事處,聶紺弩見到了周恩來。他隨即表達了欲往延安的想法。經周恩來同意與安排,聶紺弩如愿以償地與丁玲等人一起抵達延安。
延安的地域風情和抗日軍民的精神風貌猶如一股清新的氣息撲面而來。仰望巍峨聳立的寶塔山,聶紺弩興奮異常。這充滿象征意義的地標式建筑,曾經讓他的內心有過多次遐想與蕩漾。他終于見到了神仰已久的毛澤東,那是在陜北公學的開學典禮上。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隨和幽默,有領袖風度,極富個人魅力。會后,在丁玲的介紹下,聶紺弩與毛澤東近距離地見面談話。以后他曾回憶說:“和他談話得來的印象與聽講的印象很統一。他不威脅人,不使人拘謹,不使人覺得自己渺小。他自己不矜持,也不謙虛,沒有很多應酬話,卻又并不冷淡。初次見面談起來就像老朋友一樣。”不久,毛澤東請聶紺弩、丁玲等一些新近來延安的文化人吃飯。聶紺弩與毛澤東有了更近距離的接觸。在席間的輕松氣氛中,聶紺弩談了他的延安印象,并稱“中國的希望就在這里”。
但聶紺弩對延安僅僅是做一次考察,也是一個過客。他并沒有留佇延安的意思。這是因為他的心一直向往著抗戰前線。
手持周恩來介紹信,前往皖南軍部報到
聶紺弩帶著對延安的記憶再次前往西安,希冀通過周恩來的介紹直接到抗戰前線工作。
聶紺弩與周恩來可謂關系微妙。這倒不僅僅因為聶紺弩在黃埔二期時,與時任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有過接觸。而是周恩來常常戲稱聶紺弩為“妹夫”。這種指代蘊含著一層特殊的關系。
1919年,周恩來、鄧穎超、周之濂、馬駿等在天津發起組織“覺悟社”,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其中,鄧穎超與周之濂是天津女師時代的同學和閨蜜,關系十分融洽。周之濂有胞妹周之芹年僅11歲,為“覺悟社”最小成員。鄧穎超為此一直稱周之芹為“阿妹”。后來,周之芹因仰慕鄧穎超而改名為周穎。1929年,周穎成了聶紺弩的妻子。這樣,周恩來戲稱聶紺弩為“妹夫”,便有些順理成章的味道了。

聶紺弩和周穎的結婚照(1929年攝于南京)
到達西安的聶紺弩未能見到周恩來。因為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團團長已往武漢進行抗戰的統一戰線工作。聶紺弩隨即趕往武漢。
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在漢口舊日租界,一幢四層樓建筑,原為一家日本洋行。它當時也是中共代表團駐地。當時駐八路軍辦事處的中共代表團與中共長江局已合二為一,只不過對外對內叫法有別。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聶紺弩見到了周恩來,同時還意外地再次見到了他的老鄉、已擔任周恩來秘書的吳奚如。面對周恩來,聶紺弩坦言相陳,追隨而至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有機會到抗戰前線去工作。
周恩來很高興聶紺弩能有此要求。但聶紺弩畢竟屬于文人,是否適合在前線工作還不清楚。較為了解聶紺弩的吳奚如于是向周恩來建議,讓聶紺弩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周恩來知道葉挺、項英正在延攬各方面人才,覺得聶紺弩去那里也挺適合。聶紺弩的去向就這樣定了。當周恩來告知聶紺弩決定后,聶紺弩欣然同意。
皖南新四軍軍部位于環境優美的涇縣云嶺鎮羅里村。云嶺東接涇云公路,南依青弋江,西靠黃山,北望長江,疊嶂染翠的起伏山巒,茂密蔥綠的森林竹園,潺潺流水的沙石河道以及青磚黛瓦的徽派建筑,勾勒出獨特的地域風貌和魅力。葉挺曾有“云中美人霧里山”之句來贊美這樣的環境。
聶紺弩是手持周恩來介紹信來到新四軍軍部報到的,自然受到葉挺、項英的歡迎。葉挺、項英對新四軍的文化建設非常重視,當時在軍部已有很多文化人云集。聶紺弩意外遇見了以前結識的幾個左翼文學的好朋友徐平羽、丘東平、彭柏山、黃源、賴少其等人。他們都在軍部從事宣傳和敵工工作。大家聚在一起談詩論文,編輯創作,心情怡然。
皖南新四軍軍部對聶紺弩而言,是一個全新的工作環境。他在這里接觸了很多新四軍戰士,感受到他們身上那種樸實的作風和堅定的意志,以及一種積極昂揚的精神狀態。皖南的環境,皖南的戰士,皖南的氛圍,讓聶紺弩覺得一種無法自抑的創作激情呼之欲出。于是,便有了散文《巨像》《小號兵》與小說《山芋》等作品,以及《不死的槍》《收獲的季節》等詩作由心而出。這些由皖南而生創作靈感的作品,分別發表在《七月》《抗敵》《文藝陣地》等報刊上。
散文《巨像》對皖南充滿了濃烈的情感,那視野中的山影宿霧、叢竹溪流、田野村路,無不讓他情有所寄,心有所往。“我曾經看見過疏林的落日,踏過良夜的月光;玩賞過春初的山花,秋后的楓色。綠楊嫵媚,如青春少女;孤松傲岸,似百戰英雄。高峰奇詭,平嶺蘊藉,各各給人一種無言的啟示。如果一個朋友,要交往越久,才相知越深,生死患難中,才有真實的情誼;自然的奧秘也應該不是浮慕淺嘗,所可領會。那么,我對它們的低徊贊嘆,豈不是為了我和它們有了較長的往還么?”
頌吟美好景致,是為了襯托出祖國大好河山被日軍鐵蹄踐踏的嚴酷現實。
“祖國的大地整塊整塊地在魔手底下,鐵蹄底下,喘息,呻吟,顫抖,掙扎,憤怒!強盜所到的地方,縱然也是春天吧,我不相信太陽仍舊是溫暖的。”聶紺弩由此大聲吶喊,呼喚抗戰。他在皖南,在新四軍中看到了希望。置身于抗戰的隊伍中,聶紺弩突然覺得過去的“小我”,已仿佛成為一尊“人類英雄的巨像”。而這一“巨像”恰恰是整個新四軍以及抗日軍隊的群像寫真。
散文《小號兵》也是以新四軍戰士為原型,寫出小號兵的可愛以及號音的激昂嘹亮。“在他們的手上,號角閃著燦爛的金光,金光和酡顏又交織成黎明時的霞光萬道,在這泥濘的街上,竟是不曾想到的奇美,招誘著寥落的行人。那些小號兵邁著堅實而齊一腳步,踏著泥漿,踏著尚未融解的積雪,污濁的泥漿向四面飛濺,泥水把他們的膠底鞋都浸透而且吞沒了,他們毫無感覺,毫無顧恤似地,踏著號音的節拍前進”。
聶紺弩筆下那在泥濘中堅定前行的小號兵,是一種象征。那堅定中既有新四軍的抗戰英姿,也有聶紺弩的情感指向。
與《抗敵》相伴的日子,充滿和諧與溫馨
新四軍是一支有文化的軍隊。當時軍部即有一報一刊,均以“抗敵”命名,分別為《抗敵報》和《抗敵》雜志。聶紺弩的抵達很快便有了用武之地。他被任命為軍部文化委員會委員,負責《抗敵》雜志的編輯工作。聶紺弩前后共主編了三期《抗敵》。這為他的編輯生涯又增添了新的豐富內容。
《抗敵》的稿件十分豐富,雖然辦刊條件很差,紙張缺乏,印刷粗劣,沒有稿酬,但是上至軍長葉挺、支隊司令員陳毅,下至基層連排普通戰士,都是《抗敵》的熱情作者、讀者和義務通訊員,《抗敵》真正成為了官兵們離不開的刊物,大家都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它。

《抗敵報》
考慮到軍部一報一刊已經發表了不少文藝作品,軍政治部于是決定成立一個“抗敵叢書編委會”,累集這些作品,同時再組一部分新稿,出版一套抗敵叢書。籌組工作由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副團長徐平羽負責。聶紺弩自然是首選。他也成了由四人組成的編委會的負責人。其他成員分別為著名詩人辛勞以及從民運隊抽來的文學青年羅涵之(菡子)、林琳(林果)。
編委會設在一家老鄉的小屋里。小屋既是辦公室也是宿舍。進門右首的窗下,剛好放下一張長條桌,是辛勞寫作的地方。正中一張八仙桌,聶紺弩、林果、菡子各占一方。靠后邊是用木板搭架的簡易床,聶紺弩與辛勞即睡于此。
編委會是一個特別有趣與和諧的組合。聶紺弩和辛勞是著名作家、詩人,菡子與林果當時只是有著文學夢的女青年。在菡子和林果眼中,聶紺弩與辛勞是師長輩的,一起共事,不免拘謹。特別是他們對聶紺弩并不熟悉。但這種拘謹很快便蕩然無存。
當時編叢書的書稿不夠,編委會便需自己創作。還不會寫作的菡子不知如何下手,聶紺弩就告知她“寫自己想寫的東西,自已熟悉的事情。你不是做民運工作的么?那就寫在民運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好了。” 在聶紺弩的鼓勵下,菡子開始了創作。第一篇作品完成后,靦腆的她將稿子放在聶紺弩的桌子面前就跑出去了。因為心里沒底,她竟在外面躲了一天。在得到聶紺弩的肯定后,菡子無比地興奮。于是第二篇、第三篇陸續完稿,中篇、短篇、散文一瀉而下。
以后成為著名作家的菡子每每回憶這段時光,總是對聶紺弩充滿敬意和感激之情。她說:“他似乎從未向我們交待什么任務,就是叫我們寫,寫了以后,他都看得仔細,意見也提得切中要害。有一次林果給他看一篇稿子,他邊看邊問:‘是紫色的山巒么?’林果不加思索理直氣壯地指著窗外的遠山說:‘你看!不是紫色的山巒么?’老聶翻了翻眼睛,正視著林果說:‘現在是冬天,你寫的不是夏天么?’林果恍然,羞愧地說:‘對!應該是青色的。’老聶又指著一處說,‘金色的稻穗是不錯的,可你寫的是夜行軍,怎么看得見金色呢?只能聞見稻香味嘛。’他對我們的批評和鼓勵,都使人心服口服。當我們寫出好的作品,他還推薦到外面去發表。”
為了幫助年輕人提高文學修養,聶紺弩常到軍部圖書館去借《羅亭》《靜靜的頓河》《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給她們讀。菡子說:“在他指導下的寫和讀,對我們一生都起著作用。”
聶紺弩的文人風格和個性也給編委會同仁留下深刻印象。若干年后,菡子的回憶還是那么充滿細節:“老聶受不了任何約束。當時軍部很強調軍容風紀,可老聶最怕打綁腿,也很少戴軍帽,頭發七橫八豎從未認真梳理過,一件棉大衣總是掛在肩膀上。走起路來,瘦長的個子一搖一晃,腳步不緊不慢,一股悠閑勁兒。但他頭腦敏捷,語言鋒利,對事對人常常一針見血,有時又很詼諧,令人捧腹大笑,而他卻還一本正經。”
聶紺弩落拓不羈,真摯坦率,從不掩飾自己的喜怒好惡。再加上他的自由放任,在一些人眼中,難以看到他的長處,認為他狂妄不近情理,生活散漫,舊文人氣習嚴重。而常到編委會的徐平羽卻理解他、信任他、尊重和欽慕他的才華。他稱“老聶是有黃金般頭腦的人,還有一枝犀利的筆。”徐平羽知道聶紺弩的性格,盡可能給他力所能及的照顧,比如特許他不出早操,津貼費可以提前支取,發津貼時還常約聶紺弩到云嶺街上的小餐館里打牙祭。徐平羽是到編委會次數最多的人,他與聶紺弩是左聯時期的老相識。聶紺弩平時話不多,但每次徐平羽到來后,兩人便談笑風生,滔滔不絕。后來知道,徐平羽常到編委會的原因之一,就是為了給聶紺弩以友情的慰藉。菡子說:“在我們這個小集體里,當我們逐漸和他熟起來的時候,我們覺得他是平易的,是可敬可親的。”
編委會的小屋在皖南軍部還是小有名氣的,來客不在少數。年輕的女孩子們是來找菡子和林果的,同時亦想看看作家和詩人。年紀大些的多半是文人,那是聶紺弩和辛勞的朋友。有作家丘東平、彭冰山、黃源、吳強等人,他們大都在軍政治部工作,只有丘東平是做敵工工作的,但他卻是頗負盛名的報告文學作家。每每作家云集,小屋氣氛頓顯活躍、熱鬧。他們天南海北,論古道今,有時也會慷慨激昂地激烈爭辯。而多數的話題是圍繞著文學的,談作品、談作家、談書中描述的人物,談書的思想內容。小屋彌漫著濃郁的文學氣氛。
1939年2月底,周恩來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巡視和傳達中央指示。聶紺弩與編委會成員都在陳家祠堂聽了周恩來的報告。不久聽說周恩來即將離開,大家都有些茫然若失的感覺。于是,聶紺弩與大家商議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背景,創作獨幕話劇《圣誕節之夜》,獻給周恩來。聶紺弩與大家各自分工,挑燈夜干,經過一夜的的集體創作終于脫稿。第二天清晨,菡子、林果小心地將劇本訂好,在雪白的封面上扎上一根美麗的緞帶。聶紺弩磨墨執筆,在封面上書寫了劇名。最后由徐平羽親自把劇本送到周恩來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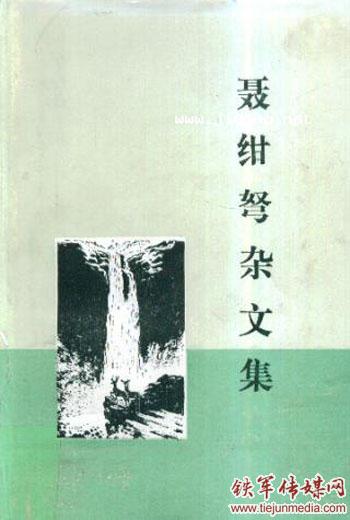
與陳毅一見如故,從詩友到“紅娘”
聶紺弩雖然已成為新四軍中的一員,但距離他向往的前線還有一步之遙。他在等待這樣的機會。
在得知常來看望的徐平羽將調往前線工作,聶紺弩不禁有些失落,畢竟知音難求,很難再有那樣激情暢敘的機會了。徐平羽行前特地邀請聶紺弩一同前往茅山根據地看看,并告訴他好友丘東平已被任命為一支隊司令員陳毅的秘書,亦將同行。這樣,聶紺弩便隨同他們一起前往茅山。
1938年6月,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率部開赴江南進行敵后抗戰,創建了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茅山山勢秀麗、林木蔥郁、峰巒疊嶂、千姿百態。主峰大茅峰,似綠色蒼龍之首,也是茅山的最高峰,海拔近四百米,雖不算高,但“山不在高,有仙則靈”。自從新四軍一支隊開辟茅山根據地后,這里就成了一片遐邇聞名的抗日熱土。
陳毅本身即為儒將,對文化人十分尊重。徐平羽、丘東平來一支隊工作即為陳毅所提議。看到他們報到,陳毅自然很高興。他甚至對丘東平說:“我們需要千百萬個作家和記者來部隊觀察體驗,盡快寫出偉大的作品來。你是最先來新四軍的作家,我由衷地希望你能多寫快寫。不過,目前還必須協助我做些對外工作,因此有必要在你這個大作家的頭銜上加上兼職兩個字。”陳毅與文化人的親近由此可見。而聶紺弩的到來完全是他即興所為,出乎陳毅預料。當然也給陳毅一個驚喜。
陳毅極善寫詩,尤其是格律詩,戎馬生涯中常吟詩作畫,是杜甫、辛棄疾、陸游的堅定“粉絲”。他身邊經常會有幾本詩詞類書,戰爭間隙開卷吟誦,心有慰藉。作為詩人的陳毅對聶紺弩早有所聞,茅山意外相見,甚感快慰。聶紺弩與陳毅可謂一見如故,詩詞成了他門之間最好的媒介。他們常秉燭夜談,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他們探求意境,切磋格律,相互唱和,抒發胸臆。陳毅的舊體詩詞創作,本來就可圈可點,如《贛南游擊詞》《梅嶺三章》等。這些詩作莫不體現出陳毅革命家的偉大情懷,也是他早年風雨漂泊的革命生涯的真實記載和情感素描。
陳毅視聶紺弩亦師亦友,感覺他們間的精神世界完全契合,都具有詩人的放達和率真的氣質。陳毅常將自己的舊作拿出來讓聶紺弩評點。聶紺弩直率的脾氣也很對陳司令員的胃口。在支隊司令部里,經常可以聽到陳毅的大嗓門:“對頭!對頭!”那是陳毅高興得意時的口頭禪。
在不長時間的接觸中,聶紺弩對陳毅非常敬佩,評價極高。他認為陳毅能文能武,是難得的一位儒將。而且陳毅從來不擺架子,生活極為簡樸,待人和藹可親,講話幽默,樂觀自信。陳毅爽朗的笑聲極富個性魅力和感染力。聶紺弩覺得來茅山最大的收獲即是結識了司令員陳毅。
不知不覺聶紺弩抵茅山已十多天,他要考慮回軍部了。陳毅很想留聶紺弩在一支隊,但他知道像聶紺弩這樣的文人并不適合在前線,甚至在部隊的生活他都有可能不適應。于是陳毅對聶紺弩說:“我看你是一位人才。如果我們打下一個縣城,或者一所大學,你去當個縣長或者校長什么的,你行!但現在是戰爭時期,又是神出鬼沒的游擊環境,行軍打仗,一天走百幾十里,你不行!你在這兒,我看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你要是想走就可以走,不要不好意思。”
陳毅的知人善任讓聶紺弩頗有感慨。他也意識到在前線自己難以發揮所長,加之頻繁的戰爭環境不可能總是充滿詩情畫意,弄不好自己會成為部隊的累贅。這樣,聶紺弩告別了茅山,告別了陳毅,領到了20塊大洋的路費,重返新四軍軍部。
與陳毅的再次見面是在春節期間,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所轄文工團在軍部演出,陳毅等前線指揮官被請到軍部會餐,觀看演出。當時,聶紺弩也應邀到現場觀看。但誰也沒想到就是這場演出卻引出了一段佳緣。
次日,陳毅看望聶紺弩,不免又談起詩作。陳毅當即將一首昨晚的新作給聶紺弩看。新詩題為《贊春蘭》,詩中寫道:“小箭含胎初生崗,似是欲綻蕊吐黃。嬌艷高雅世難受,萬紫千紅妒幽香。”顯然這是一首愛情詩,聶紺弩看出了其中端倪。
原來昨天晚上演出中,臺上一位女演員引起了陳毅注意并贏得了好感。她叫張春蘭,相貌端莊,氣質高雅,演技嫻熟。陳毅可謂一見傾心。當晚即寫下《贊春蘭》詩。
聶紺弩覺得這是好事,表示愿意來當“紅娘”,將陳毅的這份情感傳遞給她。正是聶紺弩的這份熱情,專門將陳毅的《贊春蘭》交到張春蘭手中,才挑破兩人心中那層薄紙,從而成就一段佳緣。張春蘭以后改名張茜,成為陳毅妻子。他們忠貞不渝,風雨相伴,共同走過了30多年的人生歷程。陳毅逝世后,聶紺弩專門寫有《挽陳帥》詩三首,其一為:“濁浪淘沙百戰鏖,進攻神速又迂包。江東子弟嫻兵甲,天下英雄愛塹壕。謀畫帳中虎皮椅,聲威馬上鬼頭刀。東風暮雨周郎便,打打吹吹娶小喬。”這“打打吹吹娶小喬”之句,即是對當年作為陳毅與張茜間“紅娘”歷史的回憶與注釋。

陳毅與張茜
聶紺弩剛參加新四軍時還是有新鮮感的,部隊的蓬勃朝氣、戰斗作風以及堅定的信念給他留下極深印象,他從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但時間稍長,他的不適應即體現出來。畢竟他還是文人,率性而為、我行我素,部隊的嚴謹生活和氛圍仿佛與他有些格格不入。了解他的菡子說過聶紺弩的這種不適應:“在軍營過組織生活時常常因為愛講真話而與會議組織者的意圖相沖突,嚴格的紀律他也不能適應。他骨子里其實是個自由隨性的文化人,晨昏顛倒慣了,生活上不能適應部隊生活。”這種反差決定了聶紺弩在短暫的興奮過后,開始感到些許的惘然和落寞。
聶紺弩的情緒波動終于為周恩來所知。周恩來了解聶紺弩,也覺得在前線工作可能并不適合他,而在非軍事機構從事文化工作或者創辦報刊,將更能發揮他的特長。為此,周恩來專門致電葉挺、項英,提出將聶紺弩調出新四軍的建議。電文大致內容為,如果聶紺弩在新四軍不能有很大的用處,而他本人亦想離開部隊的話,就讓他到重慶來。葉挺、項英隨即與聶紺弩談話,征詢意見。聶紺弩表示愿意前往重慶工作。葉挺、項英也很開明,在挽留未果的情況下表示尊重聶紺弩的選擇。
聶紺弩就這樣“轉業”了。他與戰友、文友依依惜別后離開了皖南,離開了新四軍。聶紺弩后來輾轉浙江金華、廣西桂林最終抵達重慶,成為由周恩來、孫科等任名譽理事、老舍任總務主任的中國抗戰文藝家協會的一名會員。聶紺弩依然用他的如椽之筆暢達胸臆,針砭時弊,呼喚抗戰。
聶紺弩仍然是一名戰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