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書鴻在工作中
“我是敦煌的癡人!”這是常書鴻的自白。老人活了整整90歲,去世前,他寫下了《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一書,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全面的回憶和總結——
自我1942年接受籌建敦煌藝術研究所的任務,1943年3月踏上敦煌的土地,至今已整整五十年了。在我生命的長河中,一大半獻給了敦煌,獻給了我所熱愛和向往的敦煌事業。無論是在戈壁敦煌,還是在異國他鄉,或在其他地方,使我魂牽夢繞的就是你——敦煌。池田大作先生曾問過我:“如果來生再到人世,你將選擇什么職業呢?”我回答說:“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來到這世界,我將還是‘常書鴻’,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這,就是“敦煌的癡人”常書鴻!就是與敦煌已經融為一體的常書鴻!
佛教界的領袖人物趙樸初給他題寫的墓碑是:“敦煌守護神”。
學術界的著名大師季羨林給他題寫的條幅是:“篳路藍縷,厥功至偉。常公大名,宇宙永垂。”
女作家葉文玲則稱呼他是“民族文化英雄”。——“走近他,就像被敦煌天樂繚繞,能深刻地感受到以他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崇高精神,感受到一種極富魅力的文化品格。”
與他同甘共苦四十八個春秋的夫人李承仙則說他是塊“奇石”,更是個徹徹底底的“杭鐵頭”。
“杭鐵頭”是杭州人對倔脾氣者——認準的事九頭牛也拉不回來、硬要梗著脖子干到底的人的一種稱呼。有關自己的這一個性,出生于杭州的常書鴻卻從“遺傳學”的角度進行了分析:“這是從祖先那兒繼承下來的秉性。”——他的祖先是馳騁在白山黑水的女真族。
的確,人們都說“性格決定命運”,更尤其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時,性格將對他的抉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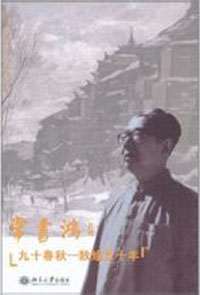
常書鴻《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封面
為了敦煌,常書鴻選擇了回國
常書鴻的女兒常沙娜曾經這樣說過:“父親生前,更多的人只知曉他是敦煌的‘守護神’、敦煌學者,他也稱自己是‘敦煌的癡人’,是大半輩子都奉獻給了敦煌的人。但是他早年留學法國,在繪畫藝術上的成就,并沒有得到美術界應有的關注和了解。”
的確,作為20世紀初即留學歐洲且研習西方繪畫藝術的青年畫家,常書鴻曾經獲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1933年至1936年間,在巴黎及里昂的春季沙龍和獨立沙龍展中,他的油畫《浴女》《病婦》和《裸女》先后獲得了金質獎章,《D夫人》和《湖畔》先后獲得了銀質獎章;1936年,他的油畫《姐妹倆》則獲得了由巴黎美術家協會頒發的金質獎章,并于巴黎國際博覽會上獲得了榮譽獎;在此期間,常書鴻還在巴黎舉辦過個人畫展,先后有五幅作品被巴黎現代美術館、蓬皮杜藝術中心和里昂市美術館收藏,且于1935年被評選為法國美術家協會超選會員及肖像畫協會的會員……這一切對于當時留學歐洲的中國畫家來說,又何嘗不是一種夢寐以求的殊榮。就連常書鴻自己也頗為得意,他不止一次地撰文寫道:“連我自己也覺得已經是蒙巴納斯(巴黎藝術家活動中心)的畫家了。”的確,此時的他已經真正進入了巴黎的主流畫界。
然而,就在常書鴻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卻毅然決然地告別了這一藝術的搖籃,回到了苦難深重的祖國。原因無他,僅僅出于一個“偶然”——在塞納河邊的一個小書攤上,他看到了被伯希和偷拍的《敦煌圖錄》;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館里,他看見了被伯希和盜竊的敦煌絹畫!


常書鴻、李承仙畫作
這對于當時的我來說真是不可思議的奇跡。因為我是一個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納斯的畫家自居,言必稱希臘、羅馬的人,現在面對祖國如此悠久燦爛的文化歷史,自責自己數典忘祖,真是慚愧之極,不知如何懺悔才是!
這一次的震驚,不僅僅是讓常書鴻發現了在自己的祖國同樣蘊藏著如此精美的藝術瑰寶,更讓他第一次認真地反省了自己的藝術觀與藝術追求——“帶著衛道者的精神和唐·吉訶德式的愚誠,在巴黎藝術的海洋中孤軍奮戰,夙興夜寐,孜孜不倦地埋頭于創作,想用自己的作品來‘挽回末世的厄運’。”就這樣,幾乎是在剎那之間,他那不遠萬里跑到西方來尋求“藝術之神”的美夢即徹底地幻滅了。
藝術上的覺醒,進一步帶來的是民族意識的覺醒。似乎也就是從這一刻開始,他厭倦了周圍的一切——“我隨著上班的人流走下蒙巴納斯地下鐵道的站口,一股混合著人體和機器散發出來的渾濁的氣味強烈地向我沖來,將近十年了,我在這座世界文明之都的巴黎每天呼吸的都是這樣的氣味啊!這時,帶著疲勞和厭倦的心情,一種難以排遣的濃烈的鄉思猛然襲擊著我的心。我默默反復地對自己說:‘祖國啊,在苦難中擁有稀世之珍的敦煌石窟藝術的祖國啊,我要為你獻出我的一切!’”
——這一年,是公元1936年。“杭鐵頭”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作出了重要的選擇。
離開世界聞名的藝術之邦,這對于已經在巴黎穩穩地扎下了根,而且是衣食無憂、家庭美滿的人來說,將意味著什么,常書鴻不是不清楚。數十年之后,他在接受日本友人池田大作的采訪時,亦開誠布公地承認了這一點——“當時,在繁華的巴黎,我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取得了一些地位。作為里昂美術家協會的會員和法國肖像畫協會的會員,我過著非常安定和舒適的生活。把這所有的優越生活丟棄,回到祖國,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而到只有流浪漢才去的、荒蕪人煙的敦煌去,就更非平常之舉了。”
的確,常書鴻所自稱的“非常安定和舒適的生活”并非一句虛言——當時前來邀請他畫肖像畫的大有人在,因為他的那幅《裸女》,被專家們評為“活脫脫是又一位出浴的維納斯”;當時將他的靜物畫或是風景畫掛在客廳墻上的也大有人在,因為他的畫風被詡為頗類于17世紀的德國畫家霍爾本。有人欣賞,就有人購買;有人購買,就有了源源不斷的收入。于是,他有條件將妻子送去學習雕塑,也有條件將女兒打扮得像童話中的公主;他更有條件住進寬敞明亮的公寓,并以中國留法藝術家學會召集人的身份,將活動的地點安排在自己的家中。1935年,教育部參事郭有守及浙江大學工學院院長李熙謀曾盛情邀請他回國執教,他沒有理睬,那時的他完全沉浸在幸福的生活與優越的環境當中。
由此可見,常書鴻為了敦煌而毅然做出回國的決定,是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的。他的妻子陳芝秀百般不能理解,他們爭吵過,紅臉過,但常書鴻的決心堅定如山:“我的理想,是將來要讓全世界的人像知道巴黎一樣知道敦煌,讓全世界的人像喜歡巴黎一樣喜歡敦煌。——但這個理想,只有回到祖國才能實現!”
如果說,是敦煌的藝術點燃了常書鴻心頭的愛國主義激情的話,那么當他踏上國土后所直面的一切,則越來越加深了他的這一情感。——1936年的東北,已經淪為了日本的殖民地,列車駛進滿洲里,常書鴻竟成為了搜查的對象。箱子被打開,書籍被抄檢,遠道而返的游子被久久地困在了火車上。1937年,北京也淪陷了,身為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的教授,常書鴻不得不背起行裝匯入到浩浩蕩蕩的流亡大軍之中。一遷江西廬山,二遷湖南沅陵,三遷云南昆明,他跟隨著學校飽嘗了顛沛流離的滋味。1939年,貴陽遭到敵機的狂轟濫炸,途經此地的常書鴻不幸中了“頭彩”,棲身的旅館被炸成了一個大洞,攜帶的行裝及書畫全部葬身火海……那天,幸逢常書鴻及妻女們都不在家,死里逃生的他立即重置了一套畫具,《是誰炸毀了我們的家》《壯丁行》《前線歸來》《湖北大捷》……他用手中的畫筆,為災難中的祖國和人民發出了吶喊。
作為“敦煌的癡人”,這時的常書鴻時刻都沒有忘記遠在戈壁沙漠中的莫高窟。侵略者的屠殺和蹂躪,加深了他對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的緊迫感與責任感;這一緊迫感與責任感,又反過來進一步加深了他對強盜們的掠奪本性的警覺與認識。他為國人開出了一張歷年來敦煌被盜的詳細清單,他更反復地提醒國人:這批強盜中有洛克濟(1879)、斯坦因(1907)、伯希和(1908)、橘瑞超(1910)、華爾納(1924)等人,他們來自英、俄、德、法、美、日、瑞典、匈牙利等國家,他們“相繼誘竊盜取,因而傳布表揚,簡直把20世紀這個‘發現時代’探險發掘的狂潮從歐洲擴展至亞洲腹地”!為此,常書鴻要迫不及待地趕往那個被強盜們時刻覬覦著的敦煌,垂涎欲滴著的敦煌,以肩負起保護民族文化遺產的重任……然而一直等到1942年,他才總算盼來了一個機會——迫于輿論的壓力,重慶國民政府終于同意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常書鴻被任命為籌備委員會的副主任。
又是一場家庭的糾紛,又是一場夫妻的爭吵。常書鴻再次發起了“杭鐵頭”的脾氣,他丟下妻兒,獨自上路了!那天——1943年的3月4日,當他經過了一個多月的顛簸,終于來到朝思暮想的敦煌,來到望眼欲穿的莫高窟時,他流下了眼淚——
……里面已經空空如也,經卷已不復存在,宛如人們搬家以后留下來的一座空房子,感到非常空寂。壁畫上的供養侍女和供養比丘尼靜靜地站在菩提樹下。供養侍女的臉上充滿善良的微笑,仿佛在向我輕聲訴說著什么:“終于把你盼來啦,我的孩子。請你自己看看吧,我很慚愧沒有能保護好這滿屋子的珍寶。我默默地站在這里,要告訴所有到這兒來的人們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為我是歷史的見證人。”那時,我自己也在心中暗暗發誓,我也要永遠站在莫高窟的大地上,使她不再遭受任何災難和蹂躪。
——這,就是常書鴻立下的誓言。
為了敦煌,常書鴻選擇了“服刑”
藝術家最愛幻想,也最多浪漫,尤其是對于長期旅居海外的人來說,竟不知敦煌除了飛天外,還有著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臨行前,友人們曾反復叮囑也反復告誡常書鴻——
徐悲鴻說:“到敦煌去是要做好受苦的準備的,要學習唐三藏——就是死活也要去取經的玄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于右任說:“在敦煌的石窟中有一幅《薩陲那太子舍身飼虎圖》。沒有看到這幅圖等于沒有到過莫高窟;到了莫高窟則一定要理解這幅圖中的深刻含義。”
張大千說:“在敦煌行使研究和保護之責,無疑是一個長期的甚至是無期的徒刑!”
常書鴻笑了,他稱自己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他回答大家道:
如果認為在敦煌工作是“徒刑”的話,那么我一輩子“無期”地干下去也在所不辭。因為這是自覺自愿、沒有人強加于我的神圣的工作!
常書鴻先從重慶乘飛機到蘭州,然后再從蘭州乘卡車繼續西行,1000多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一月之久。到達安西縣城后,再也沒有公路可以通行了,放眼望去,全是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芨芨草,于是只得改騎駱駝,120公里的路程又花去了整整四天的時間。多少年之后,常書鴻回憶起這段艱難的跋涉,不勝感慨:“離開熱鬧繁華、車水馬龍的大城市,去戈壁沙漠,感覺好像是離開了人世間的生活。”他告訴日本友人:“敦煌位于中國的西部,非常遙遠,沒有人愿意去。古詩云:‘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干。前望戈壁灘,回望鬼門關。’其實,敦煌還要在嘉峪關以西四百多公里,是一片土地荒蕪、人煙稀少的地方,這里在古代是流放犯人、遣派苦役之地,總之一句話,是任何人也不愿意去的地方。”
一路上風沙撲面,一路上饑寒交迫。常書鴻這樣描述“冷”的滋味:“在行車途中,凜冽的寒風呼嘯著吹打著面頰,以至雙耳被凍得失去了知覺,有時還疼得不得了。如果早晨要很早起來出發的話,帽檐上和眉毛上就會結滿了冰霜。每個人的面頰都因為天冷而凍得通紅……下車時,腿腳早已凍麻木,需要活動很長時間,才能開始走路。”至于“顛簸”的滋味,常書鴻同樣難以忘卻:“碰到大石頭或者小溝坎,卡車就顛晃得很厲害,人幾乎有從車上被摔下去的危險,所以大家雖說是睡覺,但還必須牢牢地抓住綁行李的繩子,否則就有可能掉下車去。到了下一個休息點的時候,大家不只是腿腳麻木,手也被凍得通紅,都腫了起來。”

莫高窟九層樓
其實,作為考驗這才剛剛開始,等到常書鴻終于站在了莫高窟的面前時,才知道一切遠非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那么浪漫——“窟前放牧著牛羊,洞窟被當作淘金沙人夜宿的地方。他們在那里做飯燒水,并隨意毀壞樹林。洞窟中流沙堆積,脫落的壁畫夾雜在斷垣殘壁中隨處皆是。洞窟無人管理,無人修繕,無人研究,無人宣傳,繼續遭受大自然和人為毀損的厄運。”
至于那里的生活,也是等到常書鴻真正安頓下來之后,才切身地體會到了什么叫做“服刑”。——莫高窟宛如一座孤島,所有的生活用品必須到15公里以外的縣城才能買到。常書鴻湊合著住在了中寺的后庭里,即那處名叫皇慶寺的以前為參拜者修建的廟宇內。沒有床,他動手和泥做成土坯,再用它們壘成一個臺子,鋪上草席,放些麥秸,便成了自己的睡鋪。沒有桌椅,他同樣用土坯壘制,再在表面涂上一層石灰,以求美觀。至于照明,則成了常書鴻最大的心患,寺廟的窗戶特別小,又沒有電燈,他只能在小碟子里倒上點油,以草莖充燈芯,制成了一盞經不住任何風吹草動的“油燈”。
“住”,是如此的簡陋;“行”,同樣是令人唏噓——剛開始什么交通工具也沒有,直至數月之后才陸續添置了兩頭驢、一頭牛、一匹棗紅馬,這竟讓常書鴻興奮得像發了一大筆橫財一樣;至于“衣”,就更不能講究了——這里的人們不分男女老幼,均以老羊皮襖御寒,毫無美感尚且不說,那一股股的膻腥味竟讓第二年來到這里的陳芝秀止不住地嘔吐起來;談到“食”,更是一言難盡——莫高窟的水是從30公里外流來的,含有大量的礦物質,苦澀異常,初來乍到的人搞不明白,為什么吃飯時總要和上一點醋,原來竟是為了起個“中和反應”;主食除了土豆便是雜糧,至于新鮮蔬菜和葷腥,根本見不到影子。那年,常書鴻三歲的兒子由于體弱多病吃不下飯,姐姐常沙娜只能四處討來一點白面,切成方塊后于爐子上焙熟,美其名曰“餅干”,以給弟弟解饞……
陳芝秀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常書鴻為什么非要把家安在這里——當年她雖然勉強同意了他的選擇,但總是希望能夠將家安在重慶,每年往敦煌跑個兩趟也就可以了;不曾想,最終不僅是常書鴻自己一去不復返,而且更將一家子人也全都“綁架”到了這個荒無人煙的地方!于是,一場家庭的悲劇終于不可避免地爆發了!——1945年的4月,陳芝秀丟下了丈夫,丟下了一雙年幼的兒女,與他人私奔了,她沒有義務在這里陪同丈夫一起“服刑”,一起“發癡”!
這一打擊對于常書鴻來說可謂致命矣,數十年后他仍然不能原諒,不能釋懷:“這對我不啻是個晴天霹靂,開始我真不知該怎么辦才好,我盡力找各種可能找到的交通工具去追趕她,可是結果茫然。最后我從馬背上摔了下來,昏倒在途中,幸而遇見長期在戈壁灘堅持工作的地質學家沈健南和一位老工人,他們救了我,把我護送回敦煌。我面臨著生活上的第一次殘酷的打擊和嚴峻考驗,像沙漠中的一陣黑旋風那樣,遮蓋了我前進的光明大道……”平心而論,陳芝秀的出走也實屬無奈,生活的艱辛只是一個方面,丈夫將所有的情感都投在了壁畫上,這不能不讓她感到失落。“一位江南的大家閨秀,一位留法的女雕塑家,能夠在莫高窟那樣的艱苦環境里堅持了近兩個春秋,也委實不簡單了。”若干年后,當常沙娜也做了母親,她才逐漸地理解了媽媽,也原諒了媽媽。
其實,這場家庭的變故也正好為常書鴻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機會——他完全可以回到重慶去,回到妻子的身邊。在那里他有一個能夠按月領取薪金的“閑職”,也有一個可以自由創作自由揮灑的畫室;他還可以賣畫,與大后方的其他文人相比,畫家們的生活相對來說還是比較無虞的。但常書鴻絲毫沒有動搖,他那“杭鐵頭”的性格也絲毫沒有改變:
在悲痛中,尤其是夜深人靜、一片肅寂,九層樓的風鐸傳來清脆的鈴聲。我凝望敦煌石窟,便產生了一種幻覺:壁畫上的飛天閃著光芒向我飛來,她們悄聲向我訴說:“你夫人離你而去,但你決不能離我們而去,決不能離敦煌而去!”
當時,我的良心深深地譴責我:“書鴻啊,書鴻,你為何回國?你為何來到這荒僻之地?堅強起來!心向不同,夫妻難為,本在情理之中。哪里跌倒,就從哪里爬起來。不論前面有多少困難,踏著堅實的大地繼續前行!”
據常沙娜回憶,此時的常書鴻創作了一幅油畫——《臨摹工作的開始》:“畫的是少女時代的我和陳延儒先生的新娘(才18歲的敦煌姑娘)。這幅畫以石青色調的‘經變’壁畫為背景,用筆瀟灑自如,著筆在人物的面部,把古代壁畫與少女們潛在的青春活力融為一體,表述了畫家對敦煌事業的未來充滿了堅定的信心。”為什么要為油畫起這么一個名字?無疑,它象征著常書鴻的“開始”——一場風暴后的重新“開始”。
就這樣,常書鴻繼續選擇著苦難,繼續選擇著“服刑”。他在庭院里栽下了一棵又一棵的果樹,他將葡萄釀制成了“常氏精制法國葡萄酒”;他既當爹又當媽,還兼當了沙娜的啟蒙老師,硬是將女兒培養成了一名出色的藝術家。1947年,命運之神終于為他送來了一位與他一樣鐵了心要來敦煌“服刑”的女學生李承仙,他們組成了新的家庭,她成了他相濡以沫的伴侶。但是殘酷的敦煌卻讓他倆又一次地付出了犧牲——襁褓中的小女兒沙妮夭折了!醫生說是軟骨病,先天的,病因源自母親懷孕期間缺少日照。常書鴻和李承仙都哭了,他倆知道這怪不得任何人,只怪自己長年累月地鉆在石窟內工作,又哪里能夠見到陽光?同仁們將這個可愛的如同小“瓷人”般的孩子葬在了莫高窟的土地上,挽聯上的落款是“孤獨貧窮的人們敬贈”……
人生是戰斗的連接。每當一個困難被克服,另一個困難便會出現。人生也是困難的反復,但我決不后退。我的青春不會再來,不論有多大的困難,我一定要戰斗到最后。
——這,就是常書鴻對待命運和苦難的回答。

常書鴻與李承仙在敦煌
為了敦煌,常書鴻選擇了堅守
其實對于每一位前來敦煌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考驗還不是生活上的艱苦,也不是工作中的艱辛,而是寂寞——遠離塵世的寂寞,背井離鄉的寂寞。
那是數十年之后的1962年,常書鴻寫下了一篇名為《喜鵲的故事》的散文。他說,不久前的一個冬天,一只孤獨的喜鵲飛到了他的窗外,這在風沙彌漫的大西北可真成了一個稀罕物。于是他每天用饅頭屑喂它,而喜鵲也成了他的“客人”,一到苦寒季節便準時來到他的窗外等待“布施”。后來,他的工作條件有了改善,不僅蓋起了汽車房,而且裝上了玻璃窗。但是不曾想,玻璃屢屢破碎,卻始終找不到原因。一天,這只喜鵲終于讓常書鴻看到了令他無比震驚的一幕——“它看了我幾眼,忽地一個健步,飛躍在汽車房前,用嘴啄在玻璃上,煩躁地叫了幾聲,跳來跳去地望著玻璃反光中它自己在杏花背景中的影子,像冬天在我窗外乞食那樣,啄一陣玻璃,又飛到樹上叫一陣,像要發生什么情況似的。我正在懷疑,說時遲,那時快,一剎那,這只瘋狂了一般的喜鵲,忽地把自己的身子,像俯沖轟炸機似地沖擊在汽車房的玻璃上。砰的一聲,玻璃碎了,喜鵲驚慌失措地振翅飛去了!”——原來是喜鵲將玻璃中的影子當成了自己的伙伴,就連它也害怕孤單啊……
其實,在常書鴻的身邊也不乏愿為敦煌效力的人,愿與他同甘共苦的人——1943年,他初次進入敦煌時,即有五個人斬釘截鐵般地跟隨著他來了;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后,又有數名昔日的學生以及美術工作者相繼來到這個荒無人煙的地方。在他們中間,盡管也有個別的心懷叵測的“騙子”,抑或自私自利的“小人”——比如說,一個搞攝影的竟把拍攝的全部資料席卷一空,一個四川大學的教授也把考察后的所有記錄竊為己有……但是,絕大多數的人是為藝術而來,是為保護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而來。
面對生活上的困難,他們無所畏懼——僅僅5萬元的開辦費,顧了這頭,顧不了那頭,但是沒有一個人叫苦,他們最大的“奢望”就是,死后能夠埋葬在有泥土的地方,不至于像敦煌這樣,除了沙還是沙。
面對工作中的困難,他們同樣勇往直前——以臨摹為例,敦煌的冬天氣溫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洞里不能生火,大家就在冰天雪地里堅持工作;洞里沒有照明設備,大家就一手端油燈,一手持畫筆;洞頂的藻井高達十余米,大家便借助鏡子,通過里面的映像進行描摹。
然而,面對孤獨和寂寞,他們卻難以忍受了——在這個方圓20公里荒無人煙的戈壁孤舟上,交通不便,信息不靈,既沒有社會活動,又沒有文體娛樂,更沒有親人團聚的天倫之樂。形影相吊的孤獨,使大家常常為等待一個親友的到來而望眼欲穿,為盼望一封家書傳遞而長夜不眠。
于是乎,他們終于一個接著一個地走了。——那是發生在1945年的冬天,先是教育部下令撤銷敦煌藝術研究所,后是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一位同仁這樣回憶道:“抗日戰爭勝利了,這消息傳到千佛洞卻是一個月以后的事,聞訊無不歡欣鼓舞,興奮之情難以言表。可是稍一定神,故鄉親人之思就頓時倍增,八年流亡他鄉的滋味應該結束了,所以人人都想東歸。先是閻文儒走了,蘇瑩輝走了,大雪紛飛中又送走了邵芳,繼之董希文夫婦帶著孩子也走了,我當然也急欲回到中原與親人團聚。潘絜茲家眷在蘭州,他當然也要走,于是我倆偕行于1946年初,告別了千佛洞。當時烏密風夫婦正在敦煌縣城,他倆聽說我們走了之后,自然也是不安于位而東歸了。就這樣,研究所的專職人員全都走光了……”這一次的打擊,委實不亞于妻子陳芝秀的出走,常書鴻的心一下子被掏得空空。1948年,他寫下了這樣一篇文章:
……一個人在沙漠單調的聲息與牲口的足跡中默默計算行程遠近的時候,那種黃羊奔竄、沙鳥悲鳴、日落沙棵的黃昏景象,使我們仿佛體會到法顯、玄奘三藏、馬可·波羅、斯文·赫定、徐旭生等那些過去的沙漠探險家、旅行家所感到的“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那般的境界。是的,我現在才了解于(右任)老先生的話:“我們這里需要對于敦煌藝術具有與宗教信仰一樣虔誠的心地的人,方能負擔長久保管的任務。”
這是常書鴻所面臨的第三次選擇——是去?是留?他仿佛真的具有了“與宗教信仰一樣虔誠的心地”。他說,他此時想起了那幅《薩陲那太子舍身飼虎圖》——“薩陲那太子可以舍身飼虎,我為什么不能舍棄一切侍奉藝術、侍奉這座偉大的民族藝術寶庫呢?在這兵荒馬亂的動蕩年代里,它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護,需要終生為它效力的人啊!”——就這樣,常書鴻再一次地選擇了堅守,而這一守就是整整五十個春秋!
常書鴻并不是佛教徒,在他的思想深處,既沒有佛學的意念,也沒有佛學的追求。他說過,敦煌藝術首先感動于他的,并非其宗教的內容,而是“偉大的中華民族堅毅、樸厚的優秀性格”。薩陲那太子的舍身精神只是其一,還有那數不清的為敦煌藝術獻出了畢生心血的古代畫工們,其不屈不撓的身影更是一種力量,一種幫助人們戰勝孤獨、戰勝困難的無形的力量。常書鴻曾作過這樣一個對比: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意大利畫家米開朗琪羅,由于成年累月地為教堂和皇宮作畫,患上了嚴重的眼疾,他的精神被后人寫進了美術史,世世代代得以傳揚;但是,“在中國,在敦煌的469個洞窟中,該有多少不知名的米開朗琪羅在沙漠邊塞中默默無言地完成著他們光輝偉大、流傳于世的創作啊!”——這便是常書鴻從敦煌壁畫中汲取到的力量。
1948年初,常書鴻將敦煌藝術研究所數年來的工作做了一個全面性的總結,并以此向全國人民進行匯報:清除石窟中的積沙10萬多立方米;修建保護性的圍墻960米;重新勘察與登記石窟465個,其中彩塑2000多座,壁畫總面積44830平方米,如果將其連接起來,足有22.5公里之長。至于臨摹與研究工作,則按計劃完成了《歷代壁畫代表作選》《歷代藻井圖案選》《歷代佛光圖案選》《歷代蓮座圖案選》《歷代線條選》《歷代建筑資料選》《歷代飛天選》《歷代山水人物選》《歷代服飾選》,以及《歷代佛教故事畫選》等十幾個專題的編輯與整理,并且還選繪了壁畫摹本800多幅,于南京、上海等地進行巡回展覽……在莫高窟長達1500多年的歷史上,這是對它所進行的第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保護和研究;是常書鴻讓它徹底結束了任人破壞、任人掠奪的歷史,是常書鴻讓它重新閃爍出了迷人的光彩!
然而,就在常書鴻成就了敦煌的同時,敦煌也同樣成就了常書鴻——它們不僅使他改變了人生觀,也使他改變了藝術觀;不僅令他開始了對于民族性格的思索,也令他開始了對于民族藝術的反思。那是抗日戰爭勝利后的1946年,孤軍奮戰中的常書鴻寫出了一篇名為《敦煌藝術與今后中國文化建設》的文章,他將燦爛的敦煌藝術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經過八年來的抵抗,勝利終于來臨。在這時候,我們應該計劃一下今后的文化建設問題。那站在前驅的藝術動向,也就是中華民族的立國基礎。我們知道,目前已是“航運”的世界,我們并不缺乏外來文化的影響,我們缺少的是引證歷史的實例、找出文化自發的力量。因為只有歷史,才能使我們鑒往知今地明白祖國的過去,明白中華民族的精神之所在。
敦煌藝術是一部活的藝術史,一座豐富的美術館,蘊藏著中國藝術全盛時期的無數杰作,也就是目前我們正在探尋著的漢唐精神的具體體現。
就這樣,常書鴻將他對敦煌的愛,深深地融入了自己的血液之中;常書鴻將他對敦煌的癡,久久地伴隨在自己的一生當中——
從那以后的半個世紀,我是踩著九層樓的風鐸聲走過來的。尤其是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獨自一人躺在床上,仰望深青色的夜空,明月皎皎,風鐸陣陣,它們仿佛在責問我:“你對敦煌藝術的保護和研究工作,干得怎樣了?”……那種凄涼的聲音給我以安慰,給我以希望,也促使我振作起來。
——這,就是常書鴻無怨無悔的心聲。

常書鴻墓地:面朝九層樓、背依三危山
常書鴻,1904年生。抗日戰爭爆發的那一年,他33歲;進入敦煌的那一年,他39歲。他沒有上過戰場,也沒有拼過刺刀,但是在這場捍衛中華民族的命運與尊嚴的戰爭中,他同樣是一名英雄,一名偉大的卻又無名的英雄!
作者小傳:

陳虹,女,江蘇作家協會會員,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化史。主要著作有:《陳白塵評傳》《管文蔚傳》《日軍炮火下的中國作家》《日軍炮火下的中國文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