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徹首徹尾的虛無主義者。”這是曹聚仁晚年時對自己的一生所做出的結論。其實早在1932年,他即在由他主編的雜志《濤聲》中開誠布公地宣示了自己的“宗旨”——不過,是借用了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中的一段話:“一個虛無派不崇拜任何權威,不人云亦云的信仰任何主義,不管那主義是怎樣的尊嚴。”
——這,就是曹聚仁,一個真真實實的曹聚仁;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一位崇尚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他說了:“我這個人,從來不領導別人,也不讓別人來領導我。”他還說了:“1924年以后,一開頭便看到了國共婚變的悲劇,所以,對于政治舞臺有了戒心,對黨爭表示十分冷淡……”為此,他曾多次遭到左翼文化陣營的批判,直至1979年還有人稱他為“反動文人”。

曹聚仁
才子曹聚仁
其實,若以名氣來講,曹聚仁可是一位頗有建樹的教授。——自1923年起,他先后在上海藝術專科學校、上海藝術大學、南洋路礦學院及暨南大學、復旦大學、大夏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教授國文,就連他自己也頗為得意地說過:“什么是教授?在資格審查項目下,首先要輪到留學歐美各國,在大學研究院獲得博士、碩士學位,或者是工程師學位的;其次才是國內大學畢業獲得學位的;又其次,才是專門研究有著作的。我呢,當然什么都不是,最多也只能算是寫稿賣文的人;然而我居然做了大學的教授,而且在文史系教授之中,區區也不算是很差的,并沒人懷疑我,以為不該擔任這樣的教職。”
其實,若以學識來講,曹聚仁亦是一位學富五車的大家。——那是1927年,他受聘為浙江省立圖書館西湖分館的館員,負責整理與校輯因兵燹而散佚的《四庫全書》。不承想,僅僅半年的時間,他竟將這部八萬卷的類書,從頭到尾地翻看了一遍,而且還指出了它所存在的三個弊病:殘、陋、錯,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了。他也很自命不凡,而且竟以顧炎武自期——“我夸下了大口,說是要寫一部有來歷而又有創見的《日知新錄》。”后來,他果然出版了《國故學大綱》《中國史學ABC》《國故零簡》;校讀了《史通》《元人曲論》《老子集注》等一系列的古籍,實不亞于清代的這名大學者。
其實,若以水平來講,曹聚仁更是一位出類拔萃的編輯。——自上個世紀30年代起,他即獨自主編過周刊《濤聲》,與徐懋庸合編過半月刊《芒種》,還擔任過半月刊《太白》的編委……他稱呼自己為“無視紳士的尊嚴,以小癟三的態度登場”,但是就連魯迅也不止一次地向他投稿,并夸贊道:“我常常看《濤聲》,也常常叫‘快哉’!”對于自己所編輯的刊物,曹聚仁是這樣總結的:“我們當時染筆的題材有三:一是魯迅所慣寫的雜文,以批評現實剖解時事為主;二是我們所寫的歷史小品,有著借古喻今的諷時意味;三是報告文字,見之于報章的特寫。”
的確,如果沒有日本侵華戰爭的爆發,曹聚仁很可能就這樣一直地走下去了——繼續做他的教授,繼續搞他的研究,繼續編他的雜志……然而,民族的危亡將他從書齋中喚醒,從“虛無”中喚醒,他不能不直面眼前的“政治”了!
那是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日軍的炮火讓他經歷了家破人亡的慘劇——
曹聚仁的那個位于上海郊區的家被摧毀了:“余于1月29日自火線中避出,真如寓所即由十九路軍借作司令部,我軍既退,仇軍又作軍部;中經便衣隊漢奸土著三次洗劫,什物書籍,蕩然一空。”
曹聚仁的那個年僅6歲的愛女夭折了:因為躲避戰火,妻子被迫將心愛的幼女帶回浙江老家。但是因水土不服,孩子懨懨成疾,再加上交通不便,求醫困難,這個活潑可愛的孩子最終夭折。曹聚仁痛不欲生,他哭泣道:“好似天地都到了末日,我這一生,也就這么完蛋了。”
最后,幾經輾轉的曹聚仁終于在上海市內一處名叫花園坊的公寓里住下了,不承想,寓所的對面竟然是三井花園!——“三井乃是日本三大企業之一,經濟侵略中國的大本營。他們的大花園,正是我們中國人血汗所喂養起來的。”曹聚仁在文章中這樣寫道。他說,園中栽滿了櫻花,雖說花期很短,但“日本人對于櫻花的贊賞,也就是對于死的贊美,這便是日本軍人的侵略精神。因此,三井花園對于我們是一種精神上的刺激。”
曹聚仁開始變了,變得幾乎判若兩人!——他自己也曾這樣總結道:“1936年以后,我的政治覺悟引我從書齋中走出,走向抗戰的洪流中去,這也正是我的生活轉折點。”
于是乎,以往從不過問政治的他參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并被推選為領導人之一。他慷慨激昂地表示:“這回抗日,乃是我們這一輩人的事;要死,我們就去死好了!”
于是乎,以往從不參加政治活動的他到處去演講,去向民眾宣傳抗日的道理和團結的重要。一次在無錫,他被當場逮捕,先是被關押在警察局,后則被送到當地駐軍第八十八師的師部。
又于是乎,堅決反對文學為政治服務的他寫下了振奮人心的救亡歌曲《戰神的腳步》:
槍在我們的肩膊,
血在我們的胸膛。
我們來捍衛祖國,
我們齊赴沙場!
渡過鴨綠江,
沖過大同江!
哈,富士山算得什么!
嘻,富士山算得什么!
我們濯足乎扶桑!
我們濯足乎扶桑!
1994年,三聯書店在出版《曹聚仁雜文集》時,夏衍親筆為它作序,他在文章里由衷地稱贊曹聚仁“始終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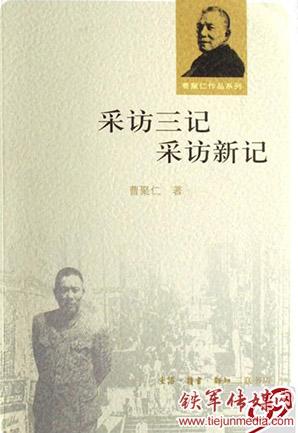
曹聚仁作品《采訪三記·采訪新記》
記者曹聚仁
的確,能夠獲得這樣的評價,是曹聚仁以自己的行動換來的;尤其是“熱烈”二字,更是他以生命換來的!——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后,他沒有像大多數文化人那樣遷徙于大后方,而是選擇了前線,選擇了做戰地記者。這不能不令所有人為之而瞠目,更為之而刮目了!
他這樣剖析自己:“抗戰給了我一個新的信念,我相信中華民族有了新的希望。我還相信抗戰的血多流一點,或許社會革命的血就可以少流一點了。因此,當時我對中國的前途一變而頗為樂觀了。”他還寫下了這樣一首詩,以示胸中的激情與抱負——
海水悠悠難化酒,書生有筆曰如刀;
戰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來付笑嘲。
但不管怎么說,上前線無疑面臨著犧牲的危險,當戰地記者也無疑要與死亡打交道。曹聚仁究竟是怎樣跨出這一步的?當年他與剛剛出獄的陳獨秀曾經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曹先生,你這樣獨往獨來是不行的!”陳獨秀批評道。
“我是一個沒有勇氣的人,我是羅亭!”曹聚仁回答。
“羅亭,最后還是參加到巴黎公社的巷戰中去了。”
“因此,我要做戰地記者。”
……
羅亭是屠格涅夫筆下的人物,他不滿現實,向往真理,卻又往往只有空談而無行動,成為了懦弱文人的一個典型。曹聚仁以羅亭自喻,這不僅表現出他與過去告別的勇氣,而且表現出他走向未來的決心。
對于這樣的選擇,就連曹聚仁的母親也不敢相信——兒子自幼膽小,甚至不敢進關帝廟,不敢看關云長的紅臉和手中的大刀——“難道你的膽子變大了?不怕死了?”這確實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直至從戰場上活著回來,曹聚仁才有了親身的體會:
上了戰場,我才恍然大悟,從將領到士兵,沒有不怕死的;在密集的火力中,不知“死亡”什么時候來叩門,哪有不怕死之理?但一上了戰場,戰斗一開始,面對著“死亡之神”,“怕”的念頭便散失掉了。“怕死不怕死”乃是一種群眾的情緒,戰號一響,提槍前進,那時候有如吃醉了似的,頗有輕快的感覺,已經和哲人一樣,到了超死生的境界了。
——就這樣,曹聚仁昂首挺胸地走上了前線,走入了“超死生的境界”:
1937年的8月,他擔任上海《大晚報》的戰地記者,并兼任《申報》《立報》及中央通訊社記者,前往淞滬前線采編戰地新聞;
1937年的10月,他受聘于金華《東南日報》,為其采寫東南各戰場的通訊報道;
1938年的2月,他受聘于中央通訊社,擔任戰地特派員,親赴臺兒莊前線進行現場報道;
1941年,他擔任贛州《正氣日報》的總經理及總編和主筆;
1944年,他接受上饒《前線日報》的編務,并擔任《前線周刊》的主筆……
整整八年的時間,他奔走于各個戰區之間,穿梭于槍林彈雨之下。其間,甚至有他為國捐軀的消息傳出,朋友們奔走相告,深表哀悼。此間,他也曾有過多次機會“改行”——1938年的春天,全國抗日救亡總會正在籌組,沈鈞儒親自上門相邀,他謝絕了;隨后,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他被推選為候補執行委員,他沒有上任……就這樣,他由一名教授、學者、編輯、作家,變成了戰地記者,變成了“有筆曰如刀”的新聞工作者!
不怕死,僅僅是戰地記者必備的條件之一;至于什么是軍事新聞,怎樣采寫軍事新聞,這對于從未上過戰場的曹聚仁來說,同樣是一個不小的考驗。然而,曹聚仁總是要比別人幸運,他結識了八十八師的師長孫元良,并與之成為摯友;于是他得以住進前線指揮部,也得以“近水樓臺先得月”——直接觀察到了戰爭,直接接觸到了戰爭,更直接從戰爭中學會了報道戰爭。他這樣總結道:“軍事新聞當然不能太真實,太真實,那就等于替敵人做情報;上海環境這么復雜,一句話都錯不得的。但同時也不能太不真實,上海的外國記者,他們有種種新聞來源;日本軍方,每天招待六次記者。豁了邊的新聞,他們理也不理。”——那么,究竟應該如何采寫呢?曹聚仁終于摸索出了自己的路子。
那是1937年的10月3日,敵方新聞發言人得意洋洋地向各國記者宣布:“閘北的中國軍隊陣地,經轟炸后完全動搖,即將向后總潰退!”當天,各家新聞媒體同時刊登了這則消息。至于它的真偽,唯有身處前線的曹聚仁一清二楚。于是乎,他以第一線記者的身份采寫出了一篇通訊——沒有一個字的反駁,沒有一個字的“辟謠”。他只是說,現在的他正在閘北的陣地上,他親眼看見了孫元良將軍,親耳聽到了旅部與團部中軍官們的談話,也親身接觸到了戰壕里眾多的士兵……這樣一篇“身臨其境”的報道,其效果恰恰在“不言而喻”,在“心照不宣”——中國軍隊已經“總潰退”的謠言,不攻自破了。
這一次的“首戰告捷”,奠定了曹聚仁成功的基礎,此后他的報道,便源源不斷地以“本報戰時通訊”的名義出現在眾多報紙的版面上。以上海發行量最大的《立報》為例,自10月1日起,頭版頭條幾乎全都包給了他。短短兩個月的時間,他一共發表了50多篇戰地通訊和特寫,其中還不包括那些數量驚人的“戰場小語”。
孫元良對此非常滿意,曹聚仁自己也頗為得意:“說實話,淞滬戰線新聞,也是我進了軍部后,才轉入正常化……”——此話不假,由于前線統帥部有令,各軍部與師部不得擅自發布軍事新聞;所有的稿件必須先向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呈報,然后轉呈上海市政府,再由新聞處向中外記者發布。這樣大的一個圈子轉下來,所有的新聞都成了舊聞,各家報紙紛紛不愿刊登,而有關淞滬前線的報道也因此幾乎成了空白。然而曹聚仁卻不同了,他是以孫元良“秘書”的身份住進司令部的,他所采寫的一切均由自己負責,與師部沒有任何關系。于是乎,他的稿件不受任何檢查,也沒有任何阻礙,不僅能夠以最快的速度與讀者見面,而且也使得淞滬前線的報道逐步轉入了“正常化”。——曹聚仁的功勞實可謂大矣!
其實,與后來的成績相比,曹聚仁在淞滬戰場僅僅是小試鋒芒,數月之后的臺兒莊大捷,則讓他大顯了一番身手。——這場中國抗戰史上的著名戰役,于1938年3月23日打響,4月7日結束,歷時兩個星期。作為中央社的戰地特派員,曹聚仁于3月25日抵達徐州,4月5日親臨臺兒莊正面戰場。這場戰役對整個局勢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各路記者蜂擁而至,其中《大公報》的范長江、《新華日報》的陸詒都是知名度很高的文化人;大家無不在暗地里較著勁,看誰的報道最快、最準。
4月5日那天,記者團到了第二集團軍軍長孫連仲的司令部,了解到臺兒莊的現狀并不樂觀,日軍已經攻占了4/5的地盤,但我軍將士仍在頑強死守。6日清晨,曹聚仁抓住機會單獨采訪了孫連仲,由此獲得了更加詳細的資料,孫將軍的態度是:“勝負之數往往就在最后五分鐘。”當時與他同樣采訪到這一新聞的,還有范長江。6日中午,三十一師師長池峰城邀請記者團到運河車站見面,不料半路遇到敵人的炮擊,只得由一位副官長草草地接待了一下。眾人頗感失望,唯獨曹聚仁沒有放過對方于閑談中的每一句話,尤其是“我們正準備反攻”這看似不經意的幾個字。此時范長江和陸詒都不在場,曹聚仁為了核實它的準確性,立即返回司令部,向參謀長金典戎做進一步的了解,他的回答是:“敵人確有撤退的趨勢。”6日晚8點25分,曹聚仁利用司令部的軍用電話向中央社徐州隨軍組報告了這一重要情報。10點,為了全面了解整個戰場的情況,尤其是側翼部隊的消息,他連夜搭乘軍車趕往120公里外的徐州,希望通過綜合戰訊,再次證實這一反攻消息的準確性。7日凌晨,曹聚仁抵達徐州,果然得到來自右翼陣地湯恩伯軍團的可靠情報:臺兒莊戰役獲得了全面勝利!……沒有一分鐘的耽擱,曹聚仁立即提筆,將這一電訊飛快地發往中央通訊社——于是乎,臺兒莊大捷的消息,就這樣通過他的筆傳遍了海內外。8日,曹聚仁再接再厲,他綜合各方面的消息,撰寫出一則長篇報道《臺兒莊巡禮記》,并由電臺發往總社。9日,全國各大報紙便紛紛刊載了出來……
曹聚仁勝利了,他終于成為了第一個報道臺兒莊大捷的記者!——范長江的長篇訪問記于《大公報》刊出時已是4月13日,陸詒的特寫在《新華日報》發表已是4月14日了。范長江委實佩服曹聚仁的神速與才華,曹聚仁則謙虛了起來:“今日之事,并不是中央社比《大公報》強,而是中央社的工具勝過了《大公報》,那是無法競爭的。”——這話也確是事實。
自1939年起,曹聚仁開始奔波于浙江、福建、江西等東南一線的各個戰區,以戰地記者的身份,撰寫出近百萬字的新聞報道、戰地雜感以及人物采訪。他稱這段生活是“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富有刺激”,“可遇而不可求”。但是就在這“刺激”與興奮的背后,又藏有多少艱辛、多少兇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身背四五十斤重的行囊,每日行軍七八十里,甚至十天半月不得休息;“有時饑渴交迫,還得在泥漿中打滾;有時走得腳腫跟破,幾乎要倒下去了;可是后有追兵,還得趕一站才憩得腳。”遇到空襲,更是命懸一線,“敵人所用的炸彈為空中爆炸彈,其爆炸為平鋪式——30度的射角,殺傷力甚強。”……這樣的生活正如他在《萬里行記》一書中所說,“無不有如在前線作戰的士兵,管不了危險不危險了”;而那些“‘坐不垂堂’的‘千金之子’,則未必肯冒這樣的危險”。
一位滿腹經綸的學者,一位體格羸弱的書生,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撐著他?是什么意志在引導著他?1940年,曹聚仁將他采寫于這一時期的通訊結集為《大江南線》,1945年,上海復興出版社再版此書時,他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這本小冊子所記的,從武漢會戰前后起,到太平洋戰爭前夜為止;這一時期,是中國抗戰最重要的時期。那時候,我國真的孤軍作戰,國際間或友或敵,都對于我們的抗戰表示絕望;國內各階層彌漫著失敗主義的空氣。武漢陷落以后,若干人士對于軍事表示絕望,竟乃脫離了陣線,走向投降的路。究竟這惡劣的情勢如何轉變過來?我們的當局如何支撐這艱苦的局面?我的新聞報道中,有著蛛絲馬跡可尋。記者個人也曾立愿,放下筆桿去肩槍炮,新的情勢誘起我的希望,鼓起勇氣在戰場上奔走著。我看了前線的實情,研究了敵人的文件,使我永遠對于抗戰前途樂觀下去。我所有的報道,決沒有夸張的成分;“時間”是最好的證明,直到今日,這本冊子的真實性并未減低,這是我自問對得起社會之處。

1957年曹聚仁與妻子鄧珂云在廬山
大師曹聚仁
對于曹聚仁的了解,應該說沒有誰能夠比得上他的妻子鄧珂云了,更何況兩人還曾并肩戰斗在臺兒莊前線以及東南各戰區。1982年,當曹聚仁的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在大陸出版時,鄧珂云于《后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抗戰八年,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是大的,對聚仁尤其如此。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正以抗戰爆發為界。……他一直稱自己為虛無主義者,是羅亭式的人物,但他又是以積極而樂觀的態度來應付人生的挑戰,使自己順應時代的潮流,把自己的一生同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聯系在一起。”
的確,戰爭能夠改變人的一生,就連曹聚仁自己不也說過,抗日戰爭“是我的生活轉折點”嗎?——在思想上,他努力擺脫“虛無主義”,擺脫“羅亭”的影響,從個人與時代的矛盾中不斷探求人生的真諦;在學術上,他努力拓展知識結構,深入進行理論研究,成為一名緊緊與時代相連的“通才”型知識分子。而后者,更該是一位文人對民族與國家應做出的貢獻——曹聚仁則真正地做到了:
第一,戰爭使曹聚仁成為了新聞戰線上的專家。
曹聚仁那一篇篇來自前線的通訊與報道使他成為了名滿天下的記者,就連朱自清也大為稱贊,并將《大江南線》中的一些篇目選為自己授課時的教材。然而,曹聚仁并沒有滿足自己,他又進一步地對新聞這一特殊的文體進行了研究,并且從理論的高度給予了歸納和總結。完稿于1939年7月1日的《新聞文藝論》,可以視作他此時的代表作。——“替后來人鋪橋梁,指示青年記者以入門的途徑,也是一件當前的切要工作。”這是他在“引子”中寫下的話,也是他撰寫此文的真正目的。
什么是“新聞”?這是他首先提出的問題——“它,并不是純文藝,乃是史筆……只要那新聞本身缺乏真實性,那篇通訊即失了意義。”作家出身的曹聚仁,準確地抓住了當時新聞寫作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并且毫無顧忌地指出了其根源之所在:“新聞記者并不是文藝作家的兼差,并不是能寫文藝作品的便可寫出優秀的新聞文藝來。”話雖說得尖刻了一點,卻是一針見血。那么,怎樣才能成為合格的新聞記者——亦即具備觀察事物的“新聞眼”呢?曹聚仁認為要從三個方面進行培養——第一,“要脫去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觀”,方能客觀地觀察與注意周圍的世界;第二,要學會“使用顯微鏡與望遠鏡”,方能全面地“鳥瞰”事件的發展動態;第三,要排除被采訪者的“主觀色彩成分”,方能辨別出新聞的真假……這些文字無一不是曹聚仁的經驗之談,既具體又真切,直到今天,還具有極其寶貴的借鑒意義。
戰爭結束以后,移居香港的曹聚仁仍在繼續他的研究。他寫下了《戰場上的文學》一書,透過歷史再次審視了當年新聞報道中存在的問題。他毫不客氣地指出——“解放區的記者,畢竟比之國軍戰區上的記者差得很遠”,“在延安那一角上,的確不曾產生一位比較有成就的新聞記者”,因為“他們一直不懂得愛倫堡的成功之處,愛氏不僅長于分析,而且善于綜合,并不以一鱗一爪的刻劃為能事”。話說得雖不受聽,但是曹聚仁的目的相當明確:作為曾經的新聞工作者,作為曾經的見證人,他將真實性與客觀性視為新聞寫作的生命,并以蘇聯著名作家、衛國戰爭時期的戰地記者愛倫堡為學習的榜樣。
第二,戰爭使曹聚仁成為了軍事方面的專家。
當年曾經流傳過這樣一個故事,叫做“曹聚仁一語救杭州”。那是1937年的11月中旬,日軍從金山衛登陸,淞滬全線開始總撤退。杭州城內一片混亂,人們紛紛舉家外逃,某些膽小者甚至已在暗中準備成立“維持會”了。此時恰逢曹聚仁路經杭州,一些頭面人物邀請他談談當前的局勢。他一手叉腰一手比劃開了:“依我看,日軍到達嘉興后,定會西折而轉攻蕪湖,以切斷我軍的退路。因此在南京保衛戰未見分曉之前,決不會進攻杭州。”他的分析有理有據,頓時穩定了眾人的情緒,而且這一預測,最終也成為了事實——日軍攻下嘉定后果然沒有南下,杭州直至一月之后才淪入敵手。
有關曹聚仁“料事如神”的例子還有不少,比如他寫的《談敵軍之用兵》一文,竟然被商務印書館選入了《戰時中學國文讀本》中。不為別的,就因為作者論點鮮明,論據充分,論證科學,足以成為中學生寫作議論文的“范本”。
曹聚仁并不是軍事學家,他何以能夠準確地預測出戰局的走向,深刻地分析出日軍“用兵”的特點?——無他,全靠“自學成才”。他從戰爭中學會了戰爭,也從戰爭中揣摩出了規律。1942年7月,他入主《正氣日報》,那一篇篇波瀾壯闊的社論——《一論戰局》《再論戰局》《三論戰局》《四論戰局》,那一篇篇鞭辟入里的時事分析——《日本進攻蘇聯乎?》《浙贛戰紀》等都出自他的筆下。如若沒有軍事家的頭腦與眼光,誰敢接受這樣的題目,并寫出如此透辟與深刻的文章?
1939年的夏末,曹聚仁來到福建省的浦城,一門心思地研究起了沿海地區的經濟狀況。不為別的,仍為解決戰爭中的一個問題——為什么日本向中國發動了大規模的“經濟戰”之后,法幣迅速貶值,金融市場一片混亂,然而卻沒有給廣大農民帶來太多的影響,也沒能摧毀廣大農村的經濟與生產?曹聚仁通過調查,終于發現了其中的“奧秘”:中國農民以自耕農為基本隊伍,中國農村以自給自足、物物交換為主要經濟形式,因此日本的經濟侵略——大批傾銷其物資,并由此而引起法幣兌換率的急劇下跌,并未給廣大農村帶來致命傷害。為此,曹聚仁得出了他的結論:中國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僅保證了廣大農民的生存,而且支撐了整個國家經濟,得以使抗戰能夠持久地進行下去。
曹聚仁的分析是否全面,是否站得住腳暫且不論,僅從他看問題的角度來說——尤其此時他并未讀到毛澤東的有關論述——確實是值得肯定的。他研究戰爭,卻沒有局限于戰場;研究軍事,卻沒有局限于軍隊。他的眼光,他的思路,當時即令新聞媒體如獲至寶——《前線日報》全文登載了這篇文章,中央社刊發了參考稿,路透社、美聯社發表了長篇專電;不久之后,中央社為此再發專電,全國各大報紙紛紛轉載,而《前線日報》則二次刊載……曹聚仁將此事視為他一生中的最高榮譽,在他眼里,后來獲得的勝利勛章難以與之相提并論。原因不在別處——他的軍事思想與戰略眼光,終于得到了社會的承認。
第三,戰爭使曹聚仁成為了史學領域的專家。
曹聚仁在史學方面的造詣遠在一般人之上,但是當年他在上海做教授時,卻沒有一所大學聘請他講授中國通史,這成了他莫大的遺憾。1946年,曹聚仁終于實現了自己的夙愿——他寫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史著:煌煌40萬言的《中國抗戰畫史》!
關于這部以畫帶史、以史入畫的巨著,當年的廣告詞是這樣寫的:“《中國抗戰畫史》由名記者曹聚仁、舒宗僑編著,中外戰地攝影記者50人合作,搜羅‘九一八’至最近珍貴照片千余幅,文字40余萬字,地圖數十幅,彩圖十余幅,直接文獻內幕秘聞百余種,為抗戰以來最完備之圖文并茂的史書。”
雖說廣告詞一般都有溢美之嫌,但是對這部書稿的介紹還是名副其實的。朱自清當年也曾致信曹聚仁,他的評價與之完全一致——“大著從‘日本社會文化與民族性’說起,使讀者對我們的抗戰有個完全的了解,這種眼光值得欽佩!書中取材翔實,圖片更可珍貴!這些材料的搜集、編排,一定費了兩位編者,特別是你,很大的心力,印刷的也很美好。我早就想我們該有這么一部畫史,現在居然看到了,真是高興,真是感謝!”
的確,曹聚仁為之付出的心血是清晰可見的——
首先,該書的史料豐富而翔實。“(民國)二十七年夏初,筆者隨軍魯南,乃開始有計劃的搜集。首重敵情,包括敵軍文件、日記、及俘虜口供;其次注意軍方文件,包括戰斗報告、實錄、命令、計劃等等;又次隨時記錄軍方人士談話,尤其注意參謀人員的議論批評;至于報紙所載電訊、通訊、特寫,連筆者所寫的在內,一律只能當作旁證……”一直以“史人”自稱的曹聚仁,確實是“有備而來”,他將撰寫抗日戰爭史當成自己的任務,而多年來的精心準備,則保證了它的資料既充實又詳盡。
其次,該書的編纂科學而合理。一向崇尚傳統史學的曹聚仁,將古代史書的三種體例——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異常靈活地運用在了《中國抗戰畫史》之中,使得前后14年的歷史脈絡清晰可察,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各個戰線的內容無一遺漏。書中既有點上的敘述,又有面上的概括;既有時間的經線,又有事件的緯線。最后還于“附錄”中收入了“各戰區將領一覽”和“抗戰大事記”,真可謂繁而不亂,雜而有章。
第三,該書的論贊客觀而公允。一部好的史書,必須有史有論,而曹聚仁的史論則隨處可見——有時是隨文而設,比如對某個戰役、某個人物的評價;有時是專題論述,比如第一章的“引論”,便是從“日本的社會、文化與民族性”、“明治維新與大陸政策”、“日本之內在的矛盾”、“甲午以來日本侵略中國之行程”、“中日糾紛與國際”等五個方面,集中地論述了日本之所以發動這場侵華戰爭的必然性。曹聚仁的論贊無不具有“史筆”之風。
——1948年的8月14日,國防部上海軍事法庭公開審判日本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諸多的證據當中,赫然地擺放著一部《中國抗戰畫史》——這便足以說明它所具有的重要價值。
——一位自稱是“虛無主義者”的知識分子,就這樣度過了他八年的抗戰歷程。究竟應該怎樣評價他呢?——他在跋山涉水報道前方戰況的同時,也曾游山玩水,極盡文人的風流與瀟灑;他在保持獨立記者身份的同時,也曾入彀“太子”蔣經國的幕府,為其主持《正氣日報》。就連曹聚仁自己也稱自己是“一個不好不壞,可好可壞,有時好有時壞的人。”
但他實實在在是“一介愛國的書生”,這是任何人也不會質疑的。“書生”是他的身份,“愛國”是他的本質;為了民族與國家的利益,他在徹底地轉變著自己——
切切實實的說,我是反對所謂“隱逸”的人生態度的;一個知識分子,當民族國家在作生死存亡的搏斗時,應當奉獻自己的一切,聽政府作有效的使用;在最緊急時,準備征集令下,也當投筆掮槍去。所謂“隱逸”,只是知識分子的巧妙遁詞;說得老實一點,便是“臨陣逃脫”,隱逸之士便是“逃兵”。
曹聚仁的這篇《從陶淵到蔡邕》,是針對陶淵明以及周作人的人生態度展開的;前者曾經是他的偶像,后者曾經是他的朋友。這段話寫于1940年的12月,該時抗日戰爭進入了最為艱苦的階段。
——曹聚仁,1900年生。“當民族國家在作生死存亡的搏斗時”,當他“聽政府作有效的使用”而奔赴前線時,年僅37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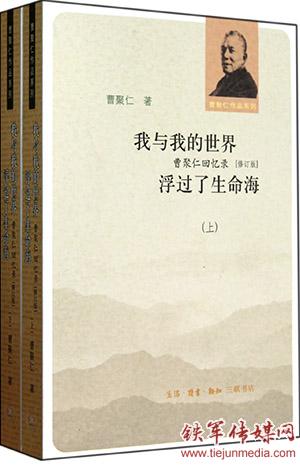
曹聚仁作品


